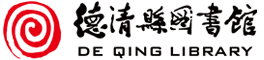【全民阅读节】张林华:风吹稻浪
发布时间:2023-06-08 | 发布人: | 点击量:1163【全民阅读节】张林华:风吹稻浪
张林华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花城》《江南》《作家》等报刊;出版有《世道人心入梦》《风雨总关情》《风起流年》等作品集;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首届“中国杂文学会鲁迅杂文奖”金奖等奖项。
风吹稻浪
文/张林华
“远处蔚蓝天空下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
爱过的地方”
——《风吹麦浪》
一首歌曲被人们接受,如同一朵鲜花、一张笑脸招人稀罕是同一个道理,自有缘由可究。寻常如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赞叹一首歌曲的魅力,因为生活中总有那么一类歌曲,常常能够在不经意间,产生某种比较特殊的、有一定柔韧度的情愫,抵达你的内心深处,要或是歌词生动令你产生某种共鸣,要或是曲调柔美常能萦绕你的耳际。在我的心目中,《风吹麦浪》 就是这样一首抒情优美的歌曲,而且,是那种舒缓柔美有张力的美,是“扑面不寒杨柳风”,美得让人舒服,爽心又悦目,既不故作深沉,卖弄技巧,也不需要歌者歇斯底里的干嚎,让人听着为之揪心,为之心累,且有一种众多歌曲所难以企及的时空意境,至于歌词,更值得一说,细腻含蓄又富有诗意,不像当下有些歌曲,词句直白单调,有些简直形同于政治口号。因之我承认有些偏爱这首歌,已记不清单曲循环聆听了多少回,只是有别于他人感受的是,每当这首优美的旋律在耳边响起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极其自然、不由分说地,浮现出一片此起彼伏、波涛汹涌的稻浪,而不是歌里唱的“麦浪”。
是的,那确实不过是身处江南,走在阡陌乡间小路上司空见惯的稻田,是一望无际、蔚为壮观的稻田,也是随风起舞,连绵翻滚,四处飘香的稻田,更是少男少女心目中,有如刻录于生命深处神曲一般的存在,纵然远隔万水千山、任时光流逝几十年,都难以忘却,无论睁眼闭眼,它“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
我想强调的只是,以我半个世纪前有限的学农劳动历练认知,并且有如进入保险柜一般,在脑海里封存数十年的认知记忆,我敢确认,那一大片在原野上无边无际地绵延连片的金色稻田,比起同等规模的青色麦田来,无疑更配得上称“浪”!
DAO
稻
LANG
浪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我开始入读初中。其时,那个特殊政治年代的革命气候已如强弩之末,渐近尾声,然而“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依旧喊得山响,在相对闭塞、信息滞后的乡村学校,依然延续着坚持所谓”开门办学”教育方针的思维惯性,同学们每学期都得排出一定时间走出教室,参加各种形式的学工学农劳动。进入初中阶段,这种活动又开始上了一个台阶,从小学时拾稻穗之类的轻微活动,变成了直接下农田参加夏收夏种劳动,强度无疑变大了,不过这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它因此也就创造了我们与广袤稻田亲密接触的机会,以及直接向农民大伯讨教劳动技能的机会,这跟稻田收割后玩儿似的,在空旷的田地里拾稻穗这样的小儿科活动相比,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所以,同学们一个个的都兴高采烈,难抑内心激动甚至有些亢奋之情。
晨光熹微的清早,同学们成群结队来到长满水稻的原野,露水泡着青草,顷刻间沾湿大家的裤脚和鞋子,不过此时谁会在乎这个呢?放眼贪婪四望,土地居然如此宽广,这也许就是想象中的天边吧?有辽阔的稻田稻浪,有无边的稻花稻香,少男少女本就柔弱的心像是瞬间就被融化了。飘舞轻纱笼罩了宽阔的田野,给大地涂上一抹金黄,阵阵微风吹来,吹拂起成片的稻穂起舞一般,此起彼伏高低错落。陈毅元帅曾有“风来凤尾罗拜忙”的诗句,原是描绘风来竹林婆娑情景的,却也完全吻合此刻这万亩稻田里的意境。“风起的时候,整片稻田的稻禾,开始以同一种节律摇摆。就像球场上的人群,向着同一个方向,一个挨一个地摆动,试图模拟潮水或海浪。广场舞这种东西,明显是水稻们做得更好。”这是我的朋友、作家周华诚在他的一篇文章里的形容,我读时对这样的表述有点意外,说不上他的表达好在哪里?只是好像从此对广场舞不再那么排斥。与熟透了的麦子依旧高昂着头的形态完全不同的是,成熟季的稻子,只有薄薄的叶片依旧如始的向上伸展着,而稻秆梢的稻穗,则总爱低下它宝贵的头颅,越是饱满的稻穗,头低得越是低,我欣赏这羞涩的弯腰,恰似那低头沉思少女的温柔,在流年里随风轻舞,若隐若现,浓郁的丰收之意展示在饱满的容颜里。这个时候的稻田,无疑也最像是一片稻的海洋,风一阵接着一阵,吹动稻叶呼啦作响,稻秆则顺势往前晃动,不过与麦子,或者青草相比,稻子的摇动幅度是有限的,明显有些矜持,而且就在劲风吹袭的间隙,前倾的稻秆会作些回摆,因为稻秆上稻穗饱满的缘故,回摆的稻秆甚至会反向弯曲,超过原来的位置,这就让稻秆连同稻穗,有了一点前倾后仰、婀娜摇曳的意思,如将审视的目光放大放高一点,你就能完完全全地欣赏到波涛一般的稻浪,汹涌澎湃,气势不凡,一层层一圈圈地在辽阔的原野上聚集着、涌动着。
扑入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里,完全就是置身于一片澎湃的稻浪中,一片散发着异香的稻海里,你首先会由衷的体味到“上风吹之,十里闻香”的真切情景。清明一过,就进入江南的水稻季,勤劳的农民们就开始张罗水稻的事。先是选种育种,再是翻地播种。时令来到初夏,农民们一边耘田,一边就开始做着收割的准备。这个时节,气温一天高过一天,水稻日生夜长,稻子渐渐抽穗,叶子渐渐变黄,眼见得丰收在望了。事实上,从种下秧苗的那一天起,如果你来到稻田,青葱的稻子有种清香就会持续散发出来,令你陶醉。稻穗的香味自然不用多说,唐朝张九龄有诗句道“绿穗靡靡,青英苾苾。”“苾”的基本字义就是芳香的意思,《荀子·礼论》 就曾说:“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稻子到了抽穗期,就到了它的发育期,芳香四溢了。不独稻穗有香气,稻子的枝干、叶片,甚至稻秆的根部,也都会散发出一种有青草味的诱人芳香,非常好闻。这种香味,干净纯粹,不混杂味,不刺激感官,是任何人工的芳香剂完全不可比及,也难以制造的香味,它是一种青葱嫩草独有的味道,稍稍带着点涩,尤其让人欲罢不能。
当然也会有宜人的清风不愿光临的时候,那多半是在酷暑三伏天。艳阳高照,从大清早就开始显示出它的凌厉威力来,空气中原本就蒸腾着一股浓烈的暑热,没有一丝风,更令人感到热气袭人,心生烦躁。白蒙蒙的天空中仅有零星几朵白云,还纹丝不动,仿佛粘贴在天幕中一般。这个时候人在大田,弯腰收割,周边为紧凑的稻穗群所围,真个是密不透风,犹如置身蒸笼一般,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内心里巴望着平地起风,如能带来一场及时雨就更好。大自然仿佛通晓人性,居然说变就变,刚刚清朗的天空,几朵黑云快速飘过,凝结上空打住,翻腾不止,太阳躲进云里,燥热的天空中,忽忽地吹来阵阵凉风,突然,电闪雷鸣,强光不停划过山野,进而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落到田埂边的几棵芭蕉叶上,滴哒滴哒地响个不停。收割中的人们,根本来不及四散躲雨,何况宽阔的田野里,几无遮蔽物,于是只一会工夫,大伙儿就都被全身上下淋了个透湿,人人皆如落汤鸡似的。久旱逢雨般,虽然狼狈不堪,同学们却没人公开叫苦的,反倒是你看看我,我指指你,一个个忍俊不禁。不过,对于成熟待割的水稻而言,暴雨光临可不是一件受欢迎的事。
江南的夏天,是台风最爱光顾的季节。天意难测,加上那时的气象科学水平还很有限,所以台风总是会不期而遇,成熟的稻子如果赶不及在台风来临前收割,会极易在强风暴的摧残下成片成片地倒伏在水田里,令收割难度加大许多,尤其此时如若再不抢收抢割,那么不消多时就会烂谷,眼看着一季的收成将泡汤,农民兄弟通常会急得跳脚,这一时节的情状,明代书画家沈周曾写有 《割稻》 诗句,“腐馀割得尚欢喜,计利当存十之五”,大致是比较真实的记录与形容。所以我们也常常会赶上台风后“抢收”水稻的劳动,就是到一块倒伏的稻田里抓紧收割水稻,这样的收割活动往往要求更高,劳动强度更大,因而记忆尤其深刻。此时的稻穗群令人甫见之下触目惊心,倒伏的稻穗依旧是连片的稻浪,只不过是凝固的稻浪,纹丝不动。雕塑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造就的,常常用不了一天的时间。某一天,狂风暴雨不期而至,在宽阔无边的田野里恣肆横行,在狂风猛烈反复的冲击下,这片刚刚成熟的稻子,被冲得东倒西歪、七零八落,待到肆虐的风雨退去,原野里呈现的,是一幅完全迥异于寻常日子的稻田景象,稻穗们或倾斜或坠地,完全不复原本骄傲直立的姿势,株株稻穗,你压着我,我托着你,抑或相互重叠缠绕出没,根本分不清你我。难得有几株稻子,显现出顽强的特性,在狂风暴雨的严峻考验面前,还依然挺立,高昂着不屈的头颅。事实上这个时候,稻子已无法论棵论株,而是连绵板结的一片,是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在强大风雨的催生下,在棵棵稻穗共同发力下,金色的稻子的海洋被固化,被塑造成了一组壮美的“稻浪”雕塑,屹立在宽广无垠的原野上。与正常站立的稻株相比,倒伏的稻穗无疑更具“稻浪”的风采,尽管不复流动摇曳的身姿,凝固的形态却更加起伏多姿,更重要的是,还多了那么一点点悲壮的色彩,令人起敬!
最适宜欣赏稻浪的时间,无疑应该是向晚时分。夏日的夕阳依旧浓烈鲜亮,来去匆匆的阵雨恰好驱赶了一点暑热,气温不再如正午那么高。这个时候,能见度最好,放眼可眺望到远处山岚起伏,云彩最是婀娜多变,大地的线条与色泽在云影的移动映衬下变得异常奇幻柔美。大自然以风、雨、光、热为画笔,点缀着辽阔的原野,大趣天成。夕阳晚霞在东南西北各处尽情挥毫,喷墨浸染,褐绿色的田野被染成金黄色,远近所有的直观神秘景观,内心所有的激动亢奋,均溶于其中,让人如痴如醉。临近黄昏时,乡村原野中,炊烟开始升起,起先只是一缕直直的青烟,升到高处,才慢慢变粗变淡,开始弯曲起伏,变成袅袅淡烟,坚决地、完全地融入到澄澈的天空里。
如同风卷残云一般,紧张的夏收劳动很快结束了农田阶段的程序,迅速转入晒谷、脱落、碾米环节。这时,稻子收割殆尽,稻草也被捆扎运走,去了各自该去的地方,田野里一片空旷宁静,零星有几只鸟儿在田里觅食,发出一两声单调的叫声,更添了一分寂寥的成分。可是,又有什么好惋惜忧愁的呢?经过了冬季土地的休眠,待来年开春时节,合着农时节气及时播下种子,精心培育到夏天,必定又将迎来一片崭新的稻浪。
DAO
稻
GE
割
当然,金色的稻浪可不是仅仅用来观赏的。收获的季节到了,及时收割,颗粒归仓就是当务之急。我们就赶在这个时候走出学堂,在老师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来到农村,开进农田,开始了辛苦而快乐的割稻劳动。高天上澄澈无比,蓝得耀眼,几乎不带一丝云彩,太阳普照大地,与我们内心涌动的热情相融相合,稻田里似乎立刻就升腾起一股难以形容的热浪。在农民大伯的指挥下,同学们走下田埂,一个连着一个,依次排开位置,摩拳擦掌,飙着劲头,有性急的同学,等不及开割的统一指令,便匆忙弯腰开始收割。不消一会工夫,原本整齐向前的队列就显出了锯齿状的前后错落,如若自空中俯视,定然是异常壮观的景象,仿佛艘艘小船,争先恐后 ,划向那浩瀚无际的稻穗的海洋。
割稻是个手工活,两只手当然都不能闲着,同时,割稻又是个技术活,需要双手配合协同发力。相对来说,右手的功能单一明确一些,就是握紧镰刀柄,待左手将长有稻穗的稻株 (也叫“稻秆”) 收拢在一起时,贴着稻株根部向左侧方向一前一后的发力,像拉锯似的,通常有那么三四下的前后划拉切割,几束稻株就被割离了生它养它的土地。割下一把稻株后,并不起身也不回头,只需扭过身子将其置于身后即可,甚至眼睛都不带看的。渐渐地,随着收割的身子不断往前推进,割下的稻株不断增多,在你的身后,就形成了一排堆得整齐有序的稻穗队列,远远望去,煞是好看。
将几棵稻株拢在一起的环节,杭嘉湖平原地区农村有一种叫法为“捏稻把”。捏住了才便于割,而怎么捏住稻株才又快又省力,方法就大有讲究,方法不同,效果也不一样。常规的方式是左手正面从稻穗间插进去,按照各自手掌的大小,抓住几束稻,通常为四至六棵左右稻株,正好一握,便于切割。另一种方式是,左手反手虎口朝下,从右面往左边用力聚拢几束稻穗,攥紧了,然后切割。这种捏稻把割稻方式的好处很明显,一是可以显著提高切割的速度,因为反手抄过去抓稻株,可以倚着左边尚挺立的稻秆,就势切割,通常可能会比前一种抓法多抓上那么一到两束稻株,积小胜为大胜,时间一久,效率自然就要高上一大截,同时,这种抓稻株的方法,还有最大的好处是相对视线好,镰刀挨着左手手背下边一点处下刀,视线不受挡,就不易割到自己的左手指。当然,事物总脱离不了两重性规律,这种割稻方式也有一定的弊病,那就是劳动强度会大许多,因为左手需要抓的稻株多了,自然就费劲,时间一长,体力下降,左手手指就会僵硬起来,虎口也会生痛不已,恰恰在这个时候也就容易出事故。
一旦左手的灵敏度下降,你双手的协调性也就同时下降,这个时候,你稍不专心,右手猛一用力,镰刀下拉处位置偏高,就很可能触到左手指,伴随着“滋啦”一声响,你感到手指一阵绞痛,匆忙间放下稻株,定睛一看,手指已被划出一道血痕,殷红的鲜血从颇深的伤口直涌出来,让你猝不及防,心慌意乱,一时手足无措。也就在转瞬之间,伤口竟已无法见到,自伤口不断涌出的鲜血已开始淤积,颜色变得更加深红起来,爬满了整只手指,于是,即便你还算胆大一点,也有些慌不择路了,顾不得手指上还沾着泥浆,就急忙将手指伸进嘴里,用嘴吮吸着止血,胆小些的同学可能就一边车转头不敢看手指,一边惊慌失措地大声喊叫起来,呼唤老师同学来帮忙止血,更有女同学甚至来不及叫唤别人帮忙,先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声痛哭起来,于是,周边的同学就都停下手里的活,赶紧聚拢过来,打探一番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帮着简单包扎一番。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大都为新发生的,也有个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再犯的,以至于渐渐地,大家都有些见怪不怪的意思,除了老师,听到来自女生的惊叫、哭喊声,也不太情愿放下手里的活,直起身子赶过来帮助,见此情景,女生也多半会识趣地止住哭声,自我处理自认倒霉罢了。这算是割稻劳动的一点苦中作乐的花絮,因为即便是一时失控发出的哭声,也会在事后转化为同学们善意调侃的笑声,这种笑声还会感染,会延续,许久许久。
割稻时站立的姿势也是颇有讲究,基本的姿势不外乎有站姿与蹲姿两种。双腿直立或稍稍弯曲站着割稻,是最常用的姿势。但站姿割稻,双脚始终得直立着,这也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尽量弯下腰,还得尽量抬起头,只有这样,你才能做到眼睛能平视前方,时间一长,脖颈可就遭罪了,更要命的还在于,当你的腰弯得差不多与地面平行时,就造成你的大半个后背就朝着天,成为承受大太阳暴晒的直接平面体,虽隔着一层为汗水湿透的衣服,你依然能结结实实体会到在烈日下,什么叫“芒刺在背”的感觉。男同学相对粗糙抗晒一点,也方便劈里啪啦地大幅度施展手脚,便大都采用这种姿势。而若持蹲姿割稻,曲着膝盖下蹲,受到太阳暴晒的面就小许多,加上一顶宽宽的草帽,基本就遮盖了你的身体,可是,由于身体重心较低,支撑点相对固定,你的身体特别是上肢,左右扭曲动弹的幅度就受限,会大大影响割稻效率,还有一点更大的弊病是,蹲的时间一长,你的膝盖、小腿可就渐渐麻木起来,待到一陇稻田好不容易割完,你突然发觉双腿完全不听你使唤,你竟然站不起身来了……
我之所以在此详尽地描述当年割稻的情景,是因为我对这段短暂的劳动经历印象深刻,也许是因为确实够累人够艰苦,又或许是因为它苦中有乐,却总透着不止一点的美好,总之是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每每会在某个宁静黝黑、月光如水的深夜里,如电影回放般一段连着一段,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地突然泛上心头,令我猝不及防,思绪纷乱,偶尔甚至可能还有极端的反应是,手指会无法克制地隐隐作痛起来,腿脚会不由自主地机械抖动起来,或者,它们会齐齐无预兆地闯入我的梦乡里,不容分说地宣示着各自的存在,令我身子一激灵,骤然梦醒。然后静坐床头,抬望窗外,见月光如水银泄地,有大美而不言,遂令脑清心净,异常宁静清醒,暗想自己这半辈子人生,无疑已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自然也过了容易脆弱的年纪,更应该警惕虚妄的矫情,立言处事理当追求一个“真”字,基于这样的立意定位,我才能确信无疑并且勇于公开强调的是,当年这段不寻常的割稻劳动经历,驱使我内心深处,至今仍对稻谷,乃至对粮食,始终保有真诚的、起码的尊重!
DAO
稻
NONG
农
烈日下暴晒劳动,难免汗流不止,一块擦汗的毛巾就是标配,且得随身带着。起初大家并无经验,不知道带的毛巾搁哪儿才好?于是都学那时风靡的样板戏里的英雄李玉和、郭建光的出场扮相,先将衬衣袖子往上挽起,两三道即可,不能挽太多,弄得跟短袖似的,便没了那股味道,再将随带的白毛巾挂在脖子上,透着一股干练劲,看上去还十分神气。可惜这套装束虽然耐看却不足取,没多长时间劳动后,就被上了一课,这才明白演戏是演戏,生活是生活,根本不是一码事嘛!因为当你弯下身子割稻时,毛巾会随着你身子的动弹而左右摆动,自然相当晃眼,一不留神,更容易割到手指,这就不光碍事了。其实,你只要将毛巾一圈一圈绕在手臂上,再将毛巾的尾部塞进绕臂几圈的里圈去,不至于使它掉落就行,这样,毛巾与手臂就融为一体,一旦汗流满面时,抬起臂来随时可擦,别提有多方便了。最终,是农民伯伯教会了我们如何处理这样的生活常识。
遇事从实际出发讲求实效,不图虚不图假,农民伯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个细微之处,言传身教着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令大家终身受益。太阳一天天升起又一天天落下,多少显得有些简单重复的劳动时间一长,新鲜劲过去,难免就有同学慢慢懈怠马虎起来,割稻的方式变得生硬粗糙了许多,农民伯伯自然都看在眼里,却并不直接批评指责,而是一遍遍耐心地提醒我们,务必将手中的镰刀尽可能贴近根部切割,这样做的直接效果是,割下的水稻秸秆就可能更长一些,其中的道理我们都懂,因为在那个年代,秸秆也被称为稻草,能当牲口饲料,能垫床取暖,最不济也能当柴火,所以稻草当然也是好东西,值钱,哪里舍得浪费那么一点点?但取用这种收割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是,你得将腰弯得更低,随着收割劳动的一分一秒持续进行,对你的腰乃至体力的考验会变得大许多,个子越高腿越长,就越是遭罪一些。与我们这些学生子相比,前来指导、带队的几位农民伯伯都是成年人,自然要高大许多,然而我们悄悄观察,从没见有一个农民大伯会在这个环节稍稍马虎半分的,后来我们渐渐明白了,那是农民朋友们的真情流露,没人不知道应该尽量轻松的道理,只是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自然更爱着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稻子,连同稻草稻秆也一样,倍加爱惜。
说是来指导如何收割,农民伯伯却并不光动动嘴,或指手画脚地教训人。每天清早下田前,农民大伯通常总是在简单交代完当天收割的注意事项后,便拎起镰刀下到田里,挨着同学一起割稻。我曾有两次与农民大伯紧挨着割稻的机会,其割稻的娴熟技术总是令我们肃然起敬,割稻的速度之快也让我们望尘莫及,“唰唰唰”的,没多大工夫,我身边的那几队列稻子已纷纷倒地,农民伯伯快速地往前收割推进,攻城略地,很快把我拉下了一大截。这多少像是一个无声却有力的提醒,催促我奋起直追,令我很有些意外的是,面前的稻株不知何时渐渐变少,稍稍望前看去,还待收割的稻田好像变得越来越窄,这意味着属于我的收割区域减小,进度自然加快许多,劳动强度也就明显减弱,暗自庆幸之余又不免疑惑,这是怎么回事呢?不由得直起身子,抬手遮光朝远处那么仔细一瞧,立刻明白了原委,原来是早已遥遥领先割稻在前的农民伯伯,顺手帮着割掉了几株原本属于我个人收割任务的稻子,一时心内五味杂陈,不知道怎么形容才好,只可惜当时既没情商也没勇气,及时说上哪怕一句感谢的话。后来在大学读到捷克作家哈谢克的一句话,产生共鸣,怀疑他是否曾经有过与我类似的生活经历,而会对某一类人肃然起敬:“有一种谦恭的默默无闻的英雄,既无拿破仑的英名,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是把这种人的品德解析一番,连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也将显得黯然失色。”许多年后同学们聚会忆旧,没想到居然有许多同学有过相似的经历,却说不出哪怕一次农民伯伯帮了我们之后而特意表白的事例,于是,一个个不免唏嘘感叹“桃李不言”,其实用心良苦,当年那好心的农民伯伯一个悄无声息的举动,何止仅仅在教会我们一种劳动技术?
是的,善良又淳朴的农民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也如这块土地和这土地上的水稻一般敦厚奉献。土地从不喧哗,却尽全力滋养了水稻,水稻也会给土地以回报,这种回报如此丰厚,又通常是朴实无华的,所以,世人才不至于感到奇怪,为什么越是成熟的稻穗,越是丰满的稻穗,头越是低垂?越不会仰起高昂的头颅,目中无人般地炫耀自己,只仿佛难以割舍生它养它的土地,而须得以这样静默深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心意。说到这里,不由得再自然不过地想起了一位功勋卓著的水稻专家,平素最反感别人称他为这个“家”那个“家”的,而总爱这样向别人介绍自己:“我只是一个种了一辈子水稻的农民。”没错,您一定也猜到了,这位谦逊的科学家就是袁隆平先生。袁隆平先生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而是广受尊重、平凡而伟大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的伟大,在于他一辈子只专注于一件事,那就是致力培育一个个优质稻种,这些优质稻种,令水稻亩产产量大幅度提升,从而让难以计数的中外家庭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还认他是一位平凡的人。他的平凡,在于他与水稻打交道一生,消耗了他毕生的精力,凝聚了他的深情实感,我相信,这是一种守成与坚持,是一种透彻领悟到了水稻珍贵,领悟到了农业精髓的大境界,才甘于并且乐于真诚的以一个农民自居。
曾经读到过袁隆平先生写给妈妈的一封信,有几句话提到他心心念念的稻谷与稻田,笔调即刻变得诗意化起来,让人一读之下印象深刻:
“稻芒划过手掌,
稻草在场上堆成垛,
谷子在阳光中哔剥作响,
水田在西晒下泛出橙黄的味道。”
(袁隆平《妈妈,稻子熟了》)
这么朴素的文字,却那么富有场景感,还透着一点点浪漫!读着这样的文字,根本用不着一段半截情景过渡,我立马可以极其逼真地闪回到某个夏日:空气里到处弥漫着丰收的气息,稻田的收割已接近尾声,田野更显得辽阔无比,晒谷场上,金黄的稻谷堆积如山,在阳光的照射下四外散发出一种带着青草气息,更多更浓沁人心脾的稻米芳香。脱落了稻谷的稻草也被勤快的人们迅速地收拢,堆积起来形成一个个草垛,在田野里静静伫立,仿佛如渐渐老去的长者,既守望着这辛劳一季的土地,又遥念起远行的孩子一般。恰在这个时候,有一位长者款款走来,在夕阳柔柔的暖光里,长者身着布衣,一脸平和,站在一小块还来不及收割的稻田里,用他那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轻轻地拂过眼前这一片熟透了的稻子,如同抚摸着孩童们年轻帅气的头颅。颗颗稻穗纷纷仰起头来,快意地接受他的亲切抚摸,旋即又低下头去,一副既亲昵又害羞的模样。长者不由得咧嘴笑了,脸上的皱纹虽然愈加明显,却显得愈加慈祥,也那么满足,全然顾不得那被换作“稻芒”的稻尖细刺,如儿童板寸头上冲天向上的头发一般,悄悄扎着他那生有老茧的手掌心。
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个温暖的世界上,还有多少人跟袁隆平一样懂水稻、爱水稻?懂它的习性、爱它的奉献?但在读到这段温暖文字的一瞬间,我就能强烈的感受到,袁隆平先生是真懂真爱,他对稻子的这一片拳拳之心,令我深深地感动,甚而至于有些心悸。
“让曾经的誓言飞舞吧
随西风飘荡
就像你柔软的长发
曾芬芳我梦乡
嗯…啦…嗯…啦…”
(《风吹麦浪》歌词)
何其庆幸,我们赖以栖身的这个平凡世界上,既有麦苗,又有稻香,有许许多多叫得上名,以及不少干脆无名无姓,在无边的旷野上自由生长、快乐生活的生物,和谐相生,构成了生物的多样性,当然,在这个广袤的星球上,还有更多如你我这样的芸芸众生,万物平等,彼此相爱相容,友善共处,虽各有功能气质不同,虽难免都要承受风吹雨打,却任谁也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比如麦苗豆青,其青葱活力总是坦然展露于明媚的春天,预报着希望与未来已来,还比如稻花飘香,常常能香满夏秋之际,一如热恋中青年男女的感官,连空气都充满了芳香,勤劳的农民爱在“稻花香里说丰年”,对他们来说,稻花香更是意味着苦尽甘来,意味着收获与甜蜜,意味着梦想成真。
我由此心生期待,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迎面吹来凉爽的风,有那么一位词曲作家,忽然灵感骤生如浪潮涌动,仿佛与我有感应一般,一气呵成,创作出一首关于稻子的优美歌曲,歌名倒可以是现成的,就叫——《风吹稻浪》。
更多精彩活动请关注
“德清县图书馆”新媒体矩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