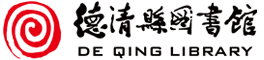【助力精神富有】活化历史文化,赋能乡村共富——诗人沈泽宜笔下的东沈村
发布时间:2021-11-07 | 发布人: | 点击量:1684助力精神富有
德清县图书馆助力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样板地建设,利用本馆馆藏文献与数据库资源,深入实地调研,梳理乡村文脉,赋能乡村共富,特别推出莫干山镇东沈村,此为第一期《诗人沈泽宜笔下的东沈村》。本期分享湖州著名诗人沈泽宜先生的《筏头寻根记》。
东沈村东与上皋坞村相邻,南与勤劳村交界,西靠安吉县,北面为筏头村。村傍溪靠山,有如桃源胜境;历史悠久,人文以南朝名相、一代辞宗沈约最为著名。
筏头寻根记
沈泽宜
2010年6月 19日,世界杯开赛第九日,我由湖州出发至德清筏头寻根,完成了我的一个多年宿愿。
1933年1月21日我出生在湖州城南一个中产家庭,湖州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我是地地道道的湖州土著。长大后我才知道沈氏宗族是由中原地区南迁至湖州的。
沈姓为黄帝(姬姓)之后,始祖姬季载为周文王第十子、周武王同母所生的最年幼弟弟。成年后随周公旦东征平叛有功,由其侄子周成王封于皖豫之间一条名为沈水的两岸地区,建立了沈国。公元前506年,即距今2516年前,沈国被晋、蔡所灭,以国为姓、不愿做亡国奴的沈氏宗室集体大逃亡,千里投亲来到了江南吴地。已建立数百年的吴国原出姬姓,由周文王大伯父、二伯父泰伯、仲雍立国,与沈氏同宗,因而当时的吴王阖闾把千里流亡的沈氏宗亲安排在了吴国西南边陲一片尚未开发的地区武康余不(即今之筏头乡),那片土地就是后来沈氏郡望吴兴郡(即今湖州市)的一部份。
繁衍生息至今沈氏已成了浙北两大城市湖州、嘉兴的第一大姓,并且由发祥地湖州同根四出,远及江苏、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东南半壁,一直扩散到全国(包括台湾)。在最新统计的全国50大姓中,沈姓人丁总数约为700万口,列第37位。与张、王、李等人丁一亿上下的大姓相比,700万的沈姓仅仅是“少数民族”,但沈姓量少质优,历朝历代都有先贤为中华文明作出过杰出贡献,我国南北朝时的一代辞宗、出生长大于武康筏头的沈约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
余生也晚,对茫如烟海、战乱频仍的我国历史知之甚少。尤其不幸的是,我家家谱已于我高祖幼年时丢失,变得来路不明了。唯一可考的是先父沈公宝如告知我的一段家族变迁史,说我们家是在太平军时由湖州城的西南方向迁入湖州的。而筏头乡的位置正好是在湖城的西南面。
太平军后期,湖州郊县曾是清军与太平军反复争夺的地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死伤惨重、十室九空的是当地老百姓。我高祖当时年仅十来岁,在全家被杀的惨痛情况下只身由西南某地逃至湖州南门城下,终因饥饿乏力倒在路边。正在其时奄奄一息的他被一位好心的大妈救活,从此渐渐长大成家立业,六传到了我这一代。
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困惑了我一生。
唯一可以作出判断的是,我们家是由湖州西南方流亡到湖城的,筏头很可能就是我家族的老根所在地。退后一步说,即使我高祖不是直接由筏头启程流亡,我更远一点的上代祖先也必定是先从筏头出发,定居湖城近郊繁衍子孙,后来才有我高祖只身流亡之举。筏头,我的根之所在,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尽管我始终翘首西南,辛苦辗转的一生中却从未有机会朝拜沈氏之根的筏头乡。这一遗憾一直到最近才得以弥补。

沈泽宜先生在筏头
6月19日,我应我80年代的学生前德清作协主席杨振华先生之邀,决定同游筏头乡以了却我多年寻根的宿愿。是日天朗气清,上午10时许抵达武康后不作停留,与振华、诗人小多、如尧由司机小王驾车,穿越104国道向筏头进发。一路苍山如黛,竹木满山,曲曲折折绕了十八弯后入山渐深,时见一汪一汪的大小溪涧在竹木掩映中清澈如梦地呈现,一股远离尘嚣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精神不觉为之一爽。小车右侧时见朴素民居,大抵建造于七、八十年代,现在已略见陈旧了。行人不多,可能都在山野间劳作或到城市务工去了。三、四十分钟后我们在乡政府前停驻,乡纪委书记盛永良先生热情相迎,一介绍才知他竟也是我校原湖州师专80年代的理科学子,小振华四、五岁光景,人非常开朗精干。
现在我终于到了祖先之地了!身处青山环抱之中,孩提般地觉得安祥舒坦,我就是从这儿流出去的源头活水的一朵小小浪花啊。我在山水之间缓步而行,每跨出一步都是一段百年历史。
一行人随后来到了沈约故居所在地东沈村。东沈村景色宜人,山环水绕中有亭翼然,但尚未题名,同行诸友遂众口一声要我担当这一使命。我素无急才,默不作答,但心中却在暗暗思忖。复行数十步,但见公路南侧立一巨石,上书“东沈村”三个红字,很是醒目,这里就是沈约的身生之地了。就在村路北侧有草坪一片,组成“沈约故居”四个大字,它的对面有平房数栊,那或许就是沈约一千六百多年前诞生的血地了。历尽沧桑的旧居门户紧闭,哑然无声,似无人居住。而在它的左手边村民修了一座说不上规模的“太公庙”,庙内供奉着沈约及其夫人的塑像,慈祥、庄肃、睿智,静观岁月。这庙不称沈公庙而称太公庙,完全符合后代沈氏的心理,太公庙要比沈公庙亲近得多了。村副支书王先生告诉我,逢年过节村民们会结伴而来朝拜这位先祖先贤,至今香火不断。我面对二尊塑像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心中在说,不肖子孙泽宜来敬拜二位老祖宗了。
按自古以来中华文化的传统习俗,一个地方要是出了一位于国于民有大功德的人,他百年之后就有可能被当地神化为庇佑一方的神灵,春秋祭祀,百代相传,“太公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人民和历史是有选择的。遗憾的是由于我家家谱早已失传,我既不可能证实也不可能证伪我是否是沈约的直系子孙了,但作为一个同在湖州这片土地上的沈姓诗人,我身上必定秉承着先祖沈约的某种气息,这是确凿无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视沈约为同宗祖先也未始不可。

沈约故里
走出太公庙后,振华对盛、王两位书记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关部门应将太公庙扩大重修,让沈约故里成为与莫干山配套的旅游景点。这一想法跟我不谋而合。谈话至此,关于亭名我也已思虑成熟。我提议将亭名定为“相约亭”,天下沈姓的发祥之地既然就在筏头乡,那么五湖四海的沈氏后人相约来此地寻根,就是一件十分自然十分有意义的事;再说相约二字中嵌着一个“约”字,会让人同时想起沈约,一语双关,比起题一个不相干的亭名要好,此其一;此外,“相”字还有看、观光,瞻仰的意思,也是跟此景此情相般配的。此话一出大家同声喊好,觉得这既避开了俗套,又与沈氏源头、沈约故居密不可分。振华补充说相还有宰相、丞相的含意,与沈约身份相当,“相约亭”三字因而有多重含义,意蕴丰厚,的确是好亭名。亭名就这样初步拟定了。
时已近午,一行人找了一家就近的小酒店共进午餐。席间我说起了一件 2003年的往事:那时我友湖州市民革副主委沈石铭先生还在世,据他说,沈氏的某一支自古迁徙到韩国(其时南北韩还统称为朝鲜)后,现已繁衍成一个颇有经济实力的庞大家族,其族长新近率领众多族人前来湖州寻根,石铭先生陪同他们到了被认为沈氏近世发祥之地的菱湖镇下昂乡竹墩村公祭沈氏始祖,堪称盛事。这真叫“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考诸史实,竹墩沈氏是中晚唐时才由武康余不迁徙来的一支,真正的古老源头不在竹墩而在筏头。个人以为两地虽然同在湖州市境内,但先后顺序、历史传承还是不可混淆的。而且竹墩的历代名人也无一可与沈约相提并论,筏头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恢复它的历史地位,至少也应该与竹墩一远一近、一西一东、一山一水交相辉映才对。这就要看德清县和湖州市今后如何操作了。
石铭先生先前还和我商议在竹墩建一道沈氏历代名人的长廊以资纪念,可惜斯人不寿,遗愿至今未能付诸实施,这也为德清县和筏头乡留下了可供继往开来的重任。
我叙述完毕后,大家感叹、议论良久,深觉要开发筏头这天下沈氏的发祥之地,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要有不可动摇的决心;二,必须有经济作后盾;三,有赖政府与民间的齐心奋斗,并辅以必要的宣传。这三点并非高不可攀,关键是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群策群力,努力使愿景成为现实,好让筏头有朝一日成为与莫干齐名的胜地。
青山依旧,绿水长流。衷心祝愿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交通方便、有必要的配套设施、面貌一新而古风犹存的新筏头能为大好河山增色,为五洲四海的沈姓后人找到一个家。
是为记。
原载《德清政协》2020年第2期
沈泽宜(1933-2014),笔名梦洲,湖州人,著名诗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师范学院教授。
德清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室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