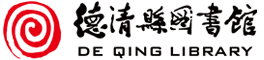【助力精神富有】活化历史文化,赋能乡村共富——下渚湖美食
发布时间:2021-09-24 | 发布人: | 点击量:1511 
德清县图书馆助力打造“无差别城乡”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样板地建设,利用本馆文献与数据库,通过采访村书记,梳理乡村文脉,赋能乡村共富,特设“助力精神富有”专栏。
下渚湖一带有特产水精灵青虾、湿地藕、防风菱,也有利用当地食材烹饪的佳肴,如鱼汤饭、鱼头面、油爆虾、红烧三角鳊鱼、浓汤鳜鱼、冬瓜煮河蚌、酱爆螺丝等等,此外,必须推荐的是别有风味的防风神茶。第四期“下渚湖美食”,邀请您共读德清县图书馆驻馆作家张抗抗美文《防风神茶》等。

【作者简介】张抗抗,著名作家,国务院参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德清县图书馆驻馆作家,其写下渚湖美文除此篇外,另有《下渚湖湿地探幽》。
防风神茶
张抗抗
知道“防风神茶”其实是2001年的春天了。此前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仅仅只听说过德清一带是“防风古国”的属地,并未听说过“防风神茶”这一古风尚存的民间饮品。

“中国烘豆茶发祥地”碑
幸而那年德清县史志办的表兄姚达人和德清县文联副主席杨振华先生来探望我母亲,带来了两盒德清三合乡自产的“防风神茶”,当我终于弄清楚这“防风神茶”即是我童年时代熟悉并喜爱的“烘豆茶”,我竟然像是见到了一位离去多年的老友,心里生出些微的感动。
小时候,每逢暑假和春节,妈妈定是要带我去德清洛舍镇的外婆家住些日子的。
在镇上的亲戚家串门,几乎家家都会给客人沏上一杯烘青豆茶。这茶必用中式的瓷盖碗沏泡,底座有托盅,掀开杯盖,瓷碗上大下小,碗口略敞,可见满至碗口三分之二处的水上,漂着几丝金黄色的橘皮和几片绿色的茶叶,一粒粒小如草籽儿的黑点点,在水中悠悠沉浮;眼神尖尖地往碗里盯下去看,有十几粒碧绿的青豆,皱皱地静卧于碗底。浅绿深绿黄绿黄黑,几种不同的色彩在水里上下晃着,很生动的样子,像一只五色斑斓的金鱼缸,煞是好看。大人说:盖上盖上,等会再喝。不多时,再次掀开碗盖,那茶水渐渐就显出颜色来了,一池清澈透亮的浅绿,从青豆里浸润出来的汁液溶在水里了。
乡里人说,这是烘豆茶。只有德清这地方的人吃呢,城里是买不到的。

小心地喝一口,一股清香味扑鼻而来。咬着一丝橘皮,滑溜溜的有些酸涩;嚼到一粒黑草籽,在齿下嘎嘣一声脆响,有奇香袭来;奇怪的是那茶水略有咸味,解渴又爽口。几道开水续过,茶水已淡,喝到见底,有人递过筷子,说你将那些青豆夹来吃罢。青豆已被茶水泡涨,肥壮饱满,吃在嘴里,韧得很有嚼头,嚼着嚼着,满嘴是香了……
曾好奇地问:这黑色的小草籽是什么呢?香得我嘴馋。
——野芝麻。乡下也叫卜芝麻,山坡地边都有,秋后剪下枝条,晾在匾中晒干了,像收油菜籽那样敲几下,一粒粒野芝麻就从荚里掉下来,形若小米,炒熟了,比芝麻还香……
烘豆茶的味道真的很特别,从此一直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可惜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烘豆茶消失得无影无踪,随后是很多年——几乎整个七八十年代全都空白。曾经问过外婆,外婆说农民的自留地都没有了,青豆自然也没有了。那些青豆采下、剥开、用盐水煮熟,然后要在微红的炭火上慢慢烘烤熏制,很费工夫的。那时候谁还有那样的闲心和工夫呢?烘豆茶就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
怅然之下,我曾以为此生再也喝不到烘豆茶了。
到了九十年代,一次回杭州探家,妈妈在厨房里忙了好一会,端出一只茶杯,很神秘地说:给你吃一样东西,是亲戚从洛舍送来的,不知你还记不记得呢?
掀开杯盖,我闻到了童年的气息,从水天一色的洛舍漾上飘来——我思念的烘豆茶,奇迹般地出现在眼前。浅绿深绿黄绿黄黑,颜色真是配得和谐沉稳,青豆橘皮野芝麻胡萝卜丝还有少许茶叶,在水中斑驳交错起伏,如同一群从远方归来的游鱼。
德清外婆家的烘豆茶回来的日子,就像外婆远去的在天之灵,重又回来看望我们了。
那以后,凡有德清老家的亲戚给妈妈送来烘豆茶,妈妈必定会分出其中一部分,亲自从邮局寄往北京。一小包绿得青翠的烘豆、一小瓶橘皮和野芝麻拌好的“调料”。然后,我独自一人在厨房来回走动,开水在炉子上响起来,还有杯盏清脆的碰撞声。我虔诚而隆重地沏泡烘豆茶,就像在完成一种神圣的祭祀仪式。
曾有一次用它来招待我的北方客人,烘豆茶端上之前,很神秘地作了渲染,示意此茶是何等珍贵。忙碌了一番之后,上茶了,客人揭开杯盖,小心啜一口,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我得意又紧张地问:怎么样,味道很特别吧?客人们面面相觑,不出声地咀嚼着,少顷,终有人忍不住反问说:这茶,怎么是咸的呢?就像菜汤,对,这明明是一碗汤嘛……
真是很扫兴。忽然明白,一个人幼年的记忆,其实是无法与人分享的。

烘豆茶之风味特色,恰恰就在微咸略苦的奇香之中。在偏爱甜食的江南,这稍带咸味的烘豆茶,确实是与众不同。其实它全部的妙处,就在于烘熏青豆以及腌制橘皮芝麻时,用了微量的盐。温温的茶水经过咽喉的那个瞬间,我能感觉到青豆在水中浸出的咸汁中所蕴含的勇气和力量,还有一种与如今江南民风迥然相异的粗犷与野性。
“防风神茶”的突然归来,令我欢喜备至。从烘豆茶到防风神茶,并非摇身一变,而是一个换回了自己原先旧衣衫的故人。几十年过去,我依然认识他,熟悉他身上飘散出的来自远古的气息,英武洒脱,然而凄然悲怆。
童年在洛舍外婆家,曾听过民间流传的有关防风氏的神话故事,可惜年代久远,竟然记不下多少了。只知防风氏是古越先祖,夏禹时代杭嘉湖地区的一位诸侯,也是治水英雄,据说身材奇高。达人表兄后来为我寄来了有关“防风氏”的资料,方知四千年前,位于钱塘江流域与太湖流域间的防风古国,其统治中心方圆百里,包括今湖州市所属德清、长兴、安吉三县。德清二都的封山(俗称防风山)、禹山(俗称长子山)和下渚湖(俗称防风湖)是当时风景幽美的地区。源自天目山的东苕溪,经瓶窑、安溪与二都下渚湖相连。近年来发掘的良渚文化遗迹,亦可寻见防风古国与其相关的种种渊源。当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末期,农业生产开始开渠排涝、养植水稻蚕桑;良渚黑陶、手工业、开矿冶炼、水上交通和舟运亦渐成气候,私有制逐步兴起,防风古国呈现出一片兴盛景象。
据《史记·国语》“孔子世家”中记载,四千多年前,中原华夏部落军事联盟的最高首领夏禹巡视江南,在今绍兴会稽山召集各地诸侯会议。“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也就是说,禹借赴会迟到之罪,杀害了防风氏,制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桩千古冤案。防风国的先民纷纷外迁出逃,防风国也因此日渐衰微……如此看来,我的德清外婆家丰饶的鱼米之乡,在远古竟然曾是一片孤独而自由的土地。后有学者认为,但凡“防风神茶”流传的地区,也是防风古国所属地域的有力佐证。
如今,在德清三合乡二都封山之麓,下渚湖之滨的防风王庙原址上,已重建起防风氏祠,再铸防风氏塑像。祠前树立了《防风神茶记》碑。碑文如下:
防风神茶记
吾乡为防风古国之封疆。相传防风受禹命治水,劳苦莫名。里人以橙子皮、野芝麻沏茶为其祛湿气并进烘青豆作茶点。防风偶将豆倾入茶汤并食之,尔后神力大增,治水功成。如此吃茶法,累代相沿,蔚成乡风。此烘豆茶之由来,或誉防风神茶。然佐料因地而异,炒黄豆、橘子皮、笋干尖、胡萝卜,不一而足,各有千秋。但均较此间烘豆茶晚出。邑产佳茗著录茶经,风味更具特色,宜乎有中国烘豆茶发祥地之桂冠也。爰为立碑纪念,茶人蔡泉宝策划,县乡领导主与其事,并勒贞珉传之久远。
丙子十月谷旦卢前撰文 郭涌书丹
从此,每逢农历八月二十五日,自发前来祭拜防风氏的乡人无数。
防风氏殁后,防风国的古代文明依然在民间流传。延至唐宋,距二都西十余里的上柏报恩寺,以及周边许多寺庙,均受防风古国地域茶文化的影响而崇尚茶道。相传历代名流如陆羽、苏轼、沈括、康熙皇帝,都曾到过防风古国地区的二都、三合、洛舍等地游玩,考察风土民情。防风古国的山水茶汁,也养育了孟郊、俞樾、俞平伯等一批杰出的文人学者。
防风氏悲壮地乘鹤西去。只有四千年前防风古国的“烘豆茶”,仍在德清一带民间流传至今。细细品尝那微咸的茶水,咀嚼着韧性的青豆橘皮,我竟闻到了血与汗的苦涩气味。我想防风氏定是死不瞑目的——也许,他留下这“防风神茶”,正是以期为世人洗心醒目。如今江南的烘豆茶风味依旧,然而,防风氏的风骨却难以寻觅了。
(原载2003年8月5日《浙江日报》)
渔人阿连
王征宇
天灰灰亮,阿连把前一晚打的鱼送到菜市时,早有老主顾在翘首。按说好的价钱,一二三过秤。现钞到手的阿连不急于回家,将留下的小份河虾、土步鱼,袋子一装,扔给面馆的老板娘,他要舒舒坦坦吃碗河鲜面,再骑摩托回去。
阿连的家在下渚湖边。爷爷辈从绍兴,一路捕鱼到此,结庐为家。不是土著,落脚地相当于从别人嘴里分了杯羹。阿连的家,落地面积大概有50平方米,一楼一底,不宽裕。

年年有余(吴文贤摄)
没钱置地重建?不是啊,辛苦点去湖里拉拉网,或蹚半天螺蛳,几百上千是稳牢牢的。说罢,五十岁的阿连露出得意的微笑。奈何阿连对渔事一点都不积极,过着“三天捕鱼两天晒网”的日子。近五平方公里的下渚湖湿地,湖汊交错,可是个聚宝盆。你懒懒散散的,被人家抢先了,不急?阿连不急,他说下渚湖的渔民谁要急了,会被骂,把鱼打少了,打没了,吃西北风去啊?——且阿连,捕了点好东西,不卖,吆喝几位好友,买点老酒,自家乐呵。就这么任性。
虽说靠水吃水,可日子没有忙碌这个词汇;日复一日的劳劳碌碌,也没有分秒必争的紧张。阿连说,赚很多钱干吗,不也就吃吃喝喝。
我小肚鸡肠地帮阿连算了算,一年下来,少说也有三四平方米商品房就这么吃吃喝喝没了,十年下来可就是个小套房。阿连有个论婚嫁的儿子,该买房买车了不是。阿连说这也不用急,当年爹妈就留条渔船给我,不也娶妻生子,日子过得好好的吗?何况儿子当过兵,还学了厨师呢,一代总比一代强。

那天晚饭,阿连烧了清蒸鳝鱼、鲇鱼烧千张、咸菜包头鱼、清烧鳜鱼……都是湖里的野生货,随便烧烧,就是顶顶赞的味道。阿连对我这个新朋友分外客气。
朋友说,你可别以为阿连没啥个性对谁都这么客气,上次有亲戚带了个城里人来吃饭,他看人家吃饭前碗筷先用开水烫烫,当时就翻脸了。嫌我家脏就别来吃饭,再没理过人家。
摊上这么不精打细算的男人,老婆没意见?阿连的老婆今年五十一,肤白泛红,风韵犹存,怎么看也就四十出头。我们吃饭她不吃,给我们倒茶倒酒添菜,施施然进出,后又抹桌子刷碗,一直笑盈盈的,看得出是个温良的女人。一个人不算计,少算计,才养生。
(原载2015年4月15日《湖州日报》)
【作者简介】
王征宇,女,笔名阿果,德清人,作家,著有《远的记忆近的生活》。

德清县下渚湖街道二都村导览图
德清县图书馆地方文献室
供稿